第一章
傑夫.溫斯頓死前,正在和妻子通電話。
妻子正說到我們需要,但傑夫再也聽不見他們需要什麼,似乎有某個重物擊中他的胸口,讓他嚥下了最後一口氣。電話筒從他手中滑落,敲碎了書桌上的玻璃紙鎮。
一週前,她才說過類似的話,她說,傑夫,你知道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嗎?接著是一陣停頓,明顯的暫停,但不像這次要命的停頓無止盡、無可更改。當時他正坐在餐桌前,琳達總愛叫這裡早餐角,儘管一點也稱不上是個獨立空間,不過是張小小的耐熱樹脂桌配上兩把椅子,笨拙地擺在冰箱左邊和乾衣機前的角落裡。說這話時,琳達正在流理檯上切洋蔥,也許是眼角的淚水讓她的問題比原先預期多了些分量,因此他覺得有必要好好想想。
傑夫,你知道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嗎?
原本他該一邊讀著休.塞迪在《時代》雜誌上討論總統大選的專欄,一邊用漫不經心、毫不關切的語氣回她,我們需要什麼,親愛的?但傑夫這天並沒有心不在焉,也沒對塞迪的閒扯蛋罵句該死。事實上,他很久很久以來都沒如此專心、集中注意力過。因此他有好些片刻沒說半句話,只是盯著琳達眼角的假淚,努力想著他們他與她到底需要些什麼?
他們需要出去透透氣,調劑生活,需要搭飛機到氣候暖和、碧綠蒼翠的小島,說不定是牙買加,或是巴貝多。自從五年前那趟計畫許久結果卻有點失望的歐洲之旅後,他們就沒再好好渡過假了。傑夫沒算上每年的佛羅里達之旅,到奧蘭多探望父母、到博卡拉頓探望琳達的家人不過是拜訪一段不斷模糊遠去的過去,沒別的了。不,他們需要的是一禮拜或一個月的時間,到頹廢墮落的異國小島上盡情逍遙:在綿延無盡的無人沙灘上做愛,晚上聽著如火紅花朵香氣飄盪在空中的雷鬼音樂。
一幢好房子也是個不錯的主意,也許是在蒙克萊登山路上的豪宅,他們多少次在禮拜天開車駛過時對此渴望不已。或是位於白原市的房子,里奇威大道上一棟十二個房間的都鐸式建築,靠近高爾夫球場。不是他想打球,不過相較於位在通往布魯克林︱皇后快速道路邊坡或是拉瓜地機場降落航線上的房子,那一片片叫楓野、威卻斯持丘的慵懶綠地才是較宜人的居住環境。
他們也需要一個孩子,琳達或許比他還急。在傑夫想像中,他們從未出世的孩子總是八歲大,跳過了需索無度的嬰兒期,但又還不到惱人的青春期。一個乖小孩,不過分漂亮或老成。是男孩女孩都不重要,只要是他們兩人的孩子,他會問逗趣的問題,會坐得靠電視機太近,舉止中會時而閃現成形中的獨特個性。
但他們不會有孩子。從一九七五年琳達子宮外孕開始,他們知道這件事不可能已經好幾年了。他們也買不起蒙克萊或白原市的房子。傑夫的職位是紐約WFYI全新聞廣播頻道的新聞總監,實際上的名聲與收入不如聽起來響亮豐厚。也許他該跳槽到電視台去,不過以四十三歲的年紀來說是不太可能了。
我們需要,需要談談,他想。他們需要直視對方的眼睛,簡單地說句:我們走不下去了。浪漫、激情、美好的計畫,沒有一樣行得通。全都變得平淡無味,而且也怪不了誰。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。
他們當然沒有談談。這正是他們最大的失敗,他們很少談及內心深處的需求,從不曾觸及始終存在兩人之間撕扯般的殘缺感。
琳達用手背拭去洋蔥引起的無意義淚水。你聽到我說的話嗎,傑夫?
是,我聽到了。
我們需要的是,她說,一邊看著他的方向,但視線不是落在他身上,一個新浴簾。
她在他步向死亡前的那通電話裡,十有八九要表達的也僅是這種層次的需求。一打蛋,或許話就這樣結束,也可能是一盒咖啡濾紙。
但他為什麼想這些?他納悶。他正在死去,看在老天分上,難道他最後不該想點更深入、更有哲理的事嗎?或是將他的畢生高潮來個快速重播,四十三年的精華剪輯。人溺死時,不都曾走過這一遭?感覺就像溺水,他在思考時,彷彿被拉長的時間一秒秒過去:那駭人的壓力、想吸口氣的絕望掙扎,使他渾身濕透的濕熱水氣,就像從他前額淌下、刺痛雙眼的鹹味汗水。
他正在溺水,正在死去。不,吃屎去,不,這不是個真實的字眼,只有花、寵物或其他人才用得上這字眼。只有老人、病人、不幸的人才會死。
他的臉落到書桌上,右頰平抵著琳達打電話來時他正要開始研讀的檔案夾。在他睜開的一隻眼睛前,紙鎮上裂開的缺口像個巨大的洞穴,世界自身的裂痕,反映他內在極度痛楚的一口破鏡。透過破碎的玻璃,他看到書架上方數位時鐘上鮮明的紅色數字:
1:06 PM OCT 1888
接下來再沒有什麼需要避免去想了,思考過程已然終止。
傑夫無法呼吸。
他當然沒辦法,他已經死了。
但是如果他已經死了,為什麼他能意識到自己無法呼吸?或意識到任何事?就死了這件事來說,這不該發生。
他從捲成一團的毯子上轉開頭,開始呼吸。悶濕的空氣中充滿了從他身上散發出的汗味。
所以他沒死。不知何故,意識到這件事並沒有讓他太興奮,就像之前的死亡假設也沒能嚇著他一樣。
也許他曾竊喜來到生命的終點。現在一切只能照舊下去:滿懷不平地承受著野心與希望落空帶來的折磨,而他再也記不得那段失敗的婚姻究竟是原因,還是結果。
他把臉上的毯子推到一旁,踢了踢起皺的床單。黑暗房間裡正播放著音樂,樂聲細不可聞。一首老歌,曲名是<嘟啦啦>,來自菲爾.史貝克特捧出來的女子樂團。
傑夫摸索著想找到電燈開關,在黑暗中完全了迷失方向。他要不是正躺在醫院的床上等著從剛才辦公室裡發生的事件中復原,要不就是在家裡,剛從比平常還恐怖的惡夢裡醒來。他的手摸到了床頭燈,開了燈。他發現自己正在一個狹小髒亂的房間裡,衣物和書散落一地,或胡亂堆在兩個相鄰的書桌上、椅子上。不是醫院也不是他和琳達的臥房,不知為何,卻有股熟悉感。
面帶微笑的裸體女郎正從貼在牆上的大照片上回望他,是《花花公子》的摺頁海報,屬於早期風格。膚色淺黑的大胸脯女郎故做正經地以腹部撐地,躺在一艘船後甲板的氣墊上,欄杆上綁著她的紅白圓點比基尼。她頭上戴了頂漂亮時髦的圓形水手帽,黑頭髮仔細做過整理和造型,使得她與年輕時的賈姬出奇相像。
他看到其他牆面也都裝飾著過時的青少年時代風格:鬥牛海報、大幅積架XK︱E黑色跑車照片、戴夫.布魯貝克的舊唱片封面。一張書桌上方有個紅白藍三色條幅,上面用星條圖案的字體寫著操!共產主義。傑夫看見那標語時笑了,他記得自己也曾從保羅.克雷斯納轟動一時的小眾雜誌《現實主義者》上訂購了一條,就跟這個一樣,那時他還在讀大學,那時
他突然直挺挺地坐起身,耳中響起突突的脈搏聲。
他還記得近門那張書桌上的老舊鵝頸燈,每當移動它時總是會從底部鬆脫。也還記得馬汀床邊地毯上有塊很大的血紅污漬沒錯,就在那裡傑夫有次偷渡茱蒂.高登上樓,茱蒂跟著漂流者的音樂繞著房間起舞,打翻了一瓶義大利紅酒留下的。
剛醒來的朦朧困惑已經消失,他現在徹底糊塗了。他匆匆掀開身上的被子下床,搖搖晃晃地走到一張書桌前,他的書桌。掃視了堆在桌上的書:《文化模式》、《薩摩亞人的長成》、《統計母體》,都是些社會學入門讀物。是丹福德還是山朋博士的課?在校園遙遠一端充滿霉味的大講堂裡,早上八點的課,他總是上完課才吃早餐。他拿起班乃迪克的書翻閱,有幾個地方已經密密麻麻地畫過了重點,書頁邊還有他手寫的筆記。
WQXI的本週熱門音樂來自水晶樂團!接下來是卡羅和寶拉點給瑪利葉塔的鮑比的歌。這些漂亮女孩們想告訴鮑比,她們的看法就跟雪紡紗樂團的女孩一樣,覺得他真是棒極了
傑夫關掉收音機,抹去前額冒出的一層汗水。他有點不自在地注意到自己已完全勃起了。還沒想到性方面的事就這麼硬,上次這樣子是多久以前了?
好了,該好好理出個頭緒來。肯定有人精心設計要捉弄他,但他不知道有誰玩整人遊戲。就算真的有,又有誰願意如此大費周章?他在上頭做過筆記的書好多年前就丟了,沒人有辦法複製得如此維妙維肖。
書桌上放著一本影印的《新聞週刊》,封面故事是西德總理康拉德.艾德諾的下臺,期號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號。傑夫一直盯著那數字,希望能為一切想出個合理解釋。
全都說不通。
房間門猛地彈開,臥室內的門把砰地撞上了書櫃。就像往常一樣。
嘿!你還在搞什麼鬼?還有十五分鐘就十一點了。我以為你十點要考美國文學。
馬汀站在門口,︱手拿了可樂一手拿了堆教科書。馬汀.貝利,傑夫大一時的室友,整個大學時代直到畢業後幾年一直是他的密友。
馬汀一九八一年自殺了,在離婚及接連的破產之後。
所以你打算怎樣?馬汀問,拿個不及格?
傑夫看著他過世已久的老友,驚訝得說不出話來:馬汀那髮線還沒後退的濃密黑髮、光滑的臉龐,尤其是那對洋溢著青春光彩、不曾見識過苦痛的眼睛。
嘿!怎麼回事?傑夫,你沒事吧?
我覺得不太舒服。
馬汀笑著把書本扔到床上。跟我說怎麼回事。我現在知道我爹為什麼警告我別碰蘇格蘭威士忌混波本酒了。喂,你昨夜在曼紐爾酒館碰上哪個甜妞兒吧?茱蒂如果在,肯定會殺了你。那女孩叫什麼?
呃
少來了,你沒醉成那樣。你會打電話給那女孩吧?
傑夫在極度驚慌中轉過身。他有太多事想告訴馬汀,但比起現在的瘋狂狀況,沒有一件事能讓人容易理解。
出了什麼事啦,老兄?你看起來他媽的糟透了。
我,呃,我得出去一下。呼吸點新鮮空氣。
馬汀一臉困惑地對他皺了皺眉頭。對,我想你需要。
傑夫抓起隨便扔在書桌前椅子上的一條卡其褲,然後打開床旁邊的衣櫃,找到一件薄棉T恤和燈芯絨夾克。
到醫務室去。馬汀說。跟他們說你感冒了,說不定蓋瑞會讓你補考。
我會。傑夫匆匆穿好衣服,套了雙馬皮便鞋,他的換氣過度症快發作了,他強迫自己得慢點呼吸。
別忘了今晚要去看希區考克的《鳥》,茱蒂跟寶拉會在杜利餐館跟我們碰面。我們要先吃點東西。
沒問題,晚點見。傑夫踏進走廊,關上身後的房門。他往下衝過三道樓梯,當經過的某個年輕人叫住他時,他敷衍地喊了聲又!回去。
宿舍大廳跟他記憶中一樣:右邊是視聽室,現在空空盪盪的,但每逢運動賽事或太空梭發射時就擠滿了人。幾個女孩聚成一團吱吱喳喳,正等著男朋友從樓上的禁地下來。布告欄上貼著學生的告示,賣車、賣書、分租公寓或徵求到馬康、沙凡納或佛羅里達的便車,對面有台可樂販賣機。
外頭的山茱萸木正值盛開季節,將校園妝點成爛漫旖旎的粉白世界,顯映著宏偉希臘羅馬式建築的白色大理石。這裡無疑是埃墨里大學,美國南方為創造出古典長春藤風格大學所精心打造的校園,好讓地方上的人也能以擁有自己的長春藤大學自豪。這類建築的永恆特質使人失去判斷力,當他緩緩穿過四方形建築,路經圖書館、法律大樓,傑夫忽然領悟,在這裡很容易把一九八八年當成一九六三年。校園廣闊綠地上,學生們正漫步閒晃,就算是從他們的衣著和髮型也找不出蛛絲馬跡。除了活像浩劫餘生的龐克造型外,八○年代年輕人流行的穿著根本和他大學早年時期沒多大差別。
老天。他想起曾經在這校圔裡度過的時光,從這裡誕生卻從未實現的夢想。那裡有座小橋通往神學院。他和茱蒂.高登曾有多少次在這裡消磨時光?再過去是心理學館,大三那年他幾乎每天都和蓋兒.班森約在那邊見面一起去吃午餐,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和女人擁有真正親密的柏拉圖式友誼。為什麼他沒從和蓋兒的友情中學到更多呢?他透過許多不同途徑,最後漂流到一個遙遠之境,遠離誕生在這寬心平靜的綠草地上、高貴建築物裡的計畫與抱負,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?
在到達主校園的入口前,傑夫已經跑了約一哩的路,他原本預期會氣喘吁吁,卻沒有。他站在格蘭紀念教堂下方的矮丘上,下望得卡圖北路和埃墨里村,那供應校園所需的小小商業區。成排的服飾店與書店看來似曾相識,其中一家哈頓藥局更是勾起他一波波的回憶:他可以在腦海中看見畫面,雜誌架、長排的白色蘇打噴泉、附有個人點唱機的紅色皮革雅座。他還能從某個雅座的桌子對面看見茱蒂.高登青春洋溢的臉龐,聞到她乾淨金髮散發的味道。
他搖搖頭,重新專注於眼前的風景。一樣,還是無法分辨現在是西元幾年。自從一九八三年美聯社舉辦恐怖主義與媒體研討會後,他就再也沒到過亞特蘭大了,而自從多久了老天,也許從他畢業一、兩年後,他就沒再回去過埃墨里大學了。他完全不知道那裡的店家是否還是老樣子,或許已經被新蓋的大樓,說不定是個購物中心取代了。
車子倒可以提供線索。他一注意到這點,就發現下面的街上看不到一輛日產或豐田。全都是老車,大多是大又耗油、在底特律生產的美國車。他看見的老車可不只是六○年代早期的車款,呼嘯而過的龐然巨獸有一堆都是五○年代的車,不過當然了,不管是一九六三年還是一九八八年,路上車齡六年、八年的車子都一樣多。
他還是沒法下定論,甚至懷疑在寢室和馬汀的短暫相遇是否只是個不尋常的逼真夢境,一個他醒來前做的夢。他現在十分清醒,而且身在亞特蘭大,這是事實,毫無疑問。也許他想藉酒澆愁,想忘卻他沉悶混亂的生活,他喝醉了,然後在一時衝動下,出於鄉愁便搭上了午夜班機來到這裡。滿街的過時車款只是個巧合。任何時候都可能會有人開著他已司空見慣的小巧日本車從眼前經過。
有個簡單方法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。他大步走下山,朝得卡圖路上的計程車招呼站走去,三輛藍白相間的計程車在排隊,他搭上最前面那輛。駕駛是個年輕人,也許是個研究生。
上哪去,老兄?
桃樹廣場飯店。傑夫對他說。
再說一次?
桃樹廣場,在市區。
我想我不知道那地方,有地址嗎?
老天爺,現在的計程車司機怎麼了?他們不該先通過考試,至少背一背城市地圖和地標嗎?
你知道麗晶酒店吧?凱悅飯店呢?
喔,對了,我知道。那是你要去的地方?
附近。
沒問題,老兄。
計程車司機往南開了幾個街區,然後在龐塞德萊昂大道右轉。傑夫伸手往屁股的口袋裡掏,忽然想到這件陌生褲子裡可能沒放錢,但他找到一個舊咖啡色皮夾,不是他的。
至少裡面有錢,兩張二十元、一張五元以及一些一元美鈔,他不必擔心付不出計程車資了。
當他把皮夾還有隨手抓來穿上的舊衣服物歸原主時,得記得把錢還給人家但是這些東西到底哪來的?主人是誰?
他打開皮夾裡的一個小格子想找答案,發現了一張埃墨里大學的學生證,上面的名字是傑佛瑞.L.溫斯頓。還找到埃墨里的圖書館借書證,一樣是他的名字。得卡圖路上一家乾洗店的收據;一小張紙巾上面寫著一個女孩名字,辛蒂,和她的電話號碼;一張父母站在奧蘭多老房子外的相片,在他父親病重前,他們一直住在那裡;一張彩色快照,照片裡的茱蒂.高登邊笑邊丟著雪球,青春歡樂的臉龐裹著一圈禦寒的外翻白毛領子。還有一張傑佛瑞.拉馬.溫斯頓的佛羅里達州駕照,有效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。
在凱悅麗晶酒店頂樓形狀像個幽浮的北極星酒吧裡,傑夫獨自坐在一張兩人座桌前,望著亞特蘭大市一望無際的天際線每四十五分鐘在身邊旋轉一圈。那位計程車司機不是沒見過世面,因為七十層樓高圓柱形的桃樹廣場飯店根本還沒蓋起來。全面國際企業的高樓、由灰石塊打造的喬治亞太平洋大廈,還有巨大黑盒子模樣的公正大樓也都消失了。整個亞特蘭大城的最高建築就在他現在所在處,寬敞的天井式大廳有抄襲其他建築的味道。在和女服務生閒聊了幾句後,事實就很明顯了,這棟飯店才剛落成,在當時仍屬於十分獨到的建築風格。
最難過的時刻莫過於傑夫看見酒吧後方鏡中的自己。他完全是有意這麼做,他當時已經很清楚自己會是什麼模樣,雖說如此,當他和鏡中那蒼白瘦長的十八歲男孩照面時,還是震驚不已。
客觀來說,鏡裡的男孩比實際年齡要蒼老些。他在那年紀時買酒很少碰上麻煩,就像現在跟這女服務生買酒一樣容易,但傑夫知道,那是因為他的身高和深陷的眼眶造成的錯覺。從他自己眼中看來,鏡中人不過是個未經世事歷練摧折的小子。
而那個年輕人正是他自己。不是記憶中的自己,而是活在此時此地的他,是鏡中那雙正握著酒杯的平滑雙手,那對正專注看著自己的銳利眼眸。
親愛的,要再來一杯嗎?
女服務生對他露出漂亮的笑容,復古的蜂窩頭及刷上厚重睫毛膏的眼睛底下,是鮮艷的紅唇。她的衣著走未來主義路線,霓虹藍的短襬洋裝看起來就像是接下來兩、三年內會在年輕女性身上見到的時尚款。
從現在起的兩、三年。那就是六○年代初了。
老天哪。
他不得不承認發生了什麼事,不可能有別的理由了。他曾經差點死於心臟病,但被救活了。一九八八年某天,他正在自己的辦公室裡,現在卻是一九六三年,而他在亞特蘭大。
傑夫怎樣也想不出一個合理解釋,連最牽強的理由都無法說明這一切。他年輕時也讀過不少科幻小說,但他曾讀過的時空旅行故事情節,沒有一個跟他現在的處境相像。他的故事裡面沒有時光機,也沒有瘋狂或其他毛病的科學家,而且也不像他狂熱閱讀的故事人物,因為他連身體都回到了年輕狀態。好像只有他的心靈穿越這些年做了時空跳躍,為了在腦海中挪出空間給十八歲的自己,他的早期意識被抹消了。
他到底是死裡逃生,還是只輕輕繞過死神身邊?在另一個未來的時間之流中,他的遺體是否正躺在紐約某個太平間裡,被病理學家的解剖刀細細切剖開來?
也許他正處於昏迷:在飽受摧殘、邁向死亡的大腦命令下,絕望地編織出一個想像的新生命。然而,但是
親愛的?女服務生詢問,要我再幫你倒一杯嗎?
呃,我,我想來杯咖啡,可以嗎?
沒問題。來杯愛爾蘭咖啡?
一般咖啡就好。加點奶精,不要糖。
來自過去的女孩端上了咖啡。傑夫凝視窗外,在逐漸黯淡的天空下,半在興建中的城市正亮起疏疏落落的燈火。
太陽消失在綿延到阿拉巴馬州的紅土山丘背後,彷彿也通向那動盪與巨變的年代、悲劇與夢想的年代。
冒蒸氣的咖啡燙傷了他的唇,他趕緊啜一小口冰水冷卻。窗外的世界不是一場夢,跟它的天真單純一樣堅實,也跟它盲目的樂觀一樣真實。
一九六三年春。
有那麼多選擇等著去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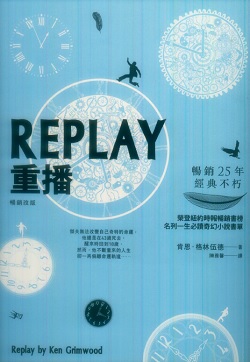
重播
肯恩.格林伍德
奇幻小說
類別- 2023-02-05發表
-
209575
完全的
© www.ifabook.com
按“左鍵←”返回上一章節; 按“右鍵→”進入下一章節; 按“空格鍵”向下滾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