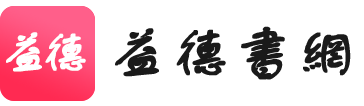漆了黑色的孔廟
東京對我好像是一個很熟悉的城市了,因為我曾經在那裏停留過多次。然而我所知道的東京,仍然是觀光客所知道的東京。一個龐大的國際性都市,有一千多萬人在裏面過著各式各樣的生活,而數百年的發展史,留下來的無數的時代的痕跡,對一個外來的過客,即使要了解一鱗半爪也是不容易的。所以這次偶然聽到東京有一座孔廟,我居然不曾去拜訪過,並沒有感到非常驚訝,只覺得有點慚愧而已。
一位日本朋友帶領我自新宿的旅社搭火車到秋葉原方向,他們的公司裏去辦事。在前一站停站的時候,我看到河川的對面山坡上是一片蓊鬱的樹木,樹叢中有些灰灰的廟宇的屋頂。他告訴我,這是孔廟(圖3)。真慚愧,來東京這麼多次,為甚麼沒有想到他們也應該有座孔廟?我大感興趣,一連問了他幾個問題,他一無所知。這只是一座孔廟而已,有甚麼好興奮的?他一生沒有進去過。然而為我的興趣所感染,同意安排利用午飯的時間,到孔廟一遊。我欣然道謝。
(圖片:東京孔廟的正門)
原來東京的孔廟,當地人稱為湯島之聖堂,難怪中國朋友在東京留學的也很少知道這裏。湯島是地名,聖堂就是聖廟。他們當年不曾把孔廟建造在東京城裏,就可說明日本人雖然尊崇儒學,並沒有把孔子神化。陪我的朋友說,在戰前這座廟非常突出,戰後東京急速發展,大廈林立,就逐漸不為人所注意了。
我們先到明治大學附近的一個小館子裏吃了午飯,乃沿著河岸步行到孔廟來。河,就是湯島川吧!雖經過都市化的嚴重破壞,還可以看到一些綠油油的楊柳。門前是一個碎石舖地的小廣場,立著一座石鋪,是大正十一年史蹟湯島聖堂碑。根據記載,湯島聖堂是十七世紀時建造的,相當於我國的明末清初。為德川幕府提倡儒學的具體措施。與一切古老建築相同,湯原聖堂經歷了多次災禍,修建了多次,早已面目全非。在三百年間的變遷,比較重要的改變,是把正殿改名為大成殿,同時卻把柱梁架構原有的紅色改為黑色。對一個中國人而言,最令人感觸萬千的,莫過於看到這些漆黑的大柱子。這樣的深沉,這樣的不可測度,為甚麼中國人從來沒有想到用黑色來建孔廟呢?
大門乃由四根粗壯的大柱子支撐著一個厚重的屋頂,黑灰的調子相當肅穆敦重,略顯得頭重腳輕。匾額是金色的仰高二字,襯在結構的黑底上,特別醒目。這座大門其實是三間,只是兩側的便門甚為矮小,易為人所忽略。這裏原應該是我國孔廟的櫺星門,通常是面闊三間並列,以氣派勝。比較起來,這裏顯得局面不夠壯闊。走近了,知道粗大的結構是鋼骨水泥改建的。
進了大門,要走幾十公尺略加曲折的石版路,登幾十步石階。右轉才是孔廟中軸線上的正門,入德門。大殿背山面河而建,前低後高,正門已經接近河岸了。然因地勢高,自仰高門進來,還要上登幾十階。沿途的環境感覺綠蔭相夾,靜寂之至,倒像一座佛寺。
入德門是孔廟中僅有的一座木造建築,是十八世紀最後一次大修時的遺物,被列為重要文化財,附近不准吸煙。也許因為是古物,這座門的規模與氣派不如仰高門遠甚。同樣的黑色木構架,灰色瓦屋頂,單開間,但顯得細緻輕巧些。而尤其是木構造的若干接頭使用銅件,梁架上、柱頭上,及搏風板都有精美的雕刻,與我國的建築相近而不相同,而尤有古風。可惜為了保護該建築而加的銅質天溝與水落,影響了建築的外觀。這在我國,恐怕是不能為大眾所容忍的。
進了入德門之後,要爬一個臺階,才能到達正殿的廣場。臺階兩側林木茂盛,但因為自門口即可看到遠處最後一進大成殿的匾額,空間的連續感還是很緊湊的。而中國孔廟中所沒有的高差,卻予人一種仰高的感受。爬上臺階,就到了我國孔廟中大成門的前面。而在這裏,臺階上是一個花崗石鋪的廣場,正面的建築,為五開間三門歇山頂,匾額上金書杏壇二字。我孤陋寡聞,從來沒聽過孔廟中有用這兩個字為額的,覺得很新鮮。
杏壇的三間門,只有中央一間是開著的,因此可以看到大殿及其兩廂的外貌,但卻用繩子攔著,不准參觀。如果沒有日本人陪我,說不定偷溜進去瞻仰一番大成殿中的景象。
大成殿是五開間單檐歇山頂,屋頂比例相當舒展,正脊兩端有非常特殊的鴟尾。灰綠色的屋瓦,黑色的柱梁,灰色花崗石的正庭鋪面,整個感覺是溫和而又嚴肅的。大殿前沒有月臺,又沒有前廊,所以顯得臺基不夠寬大。在造形的意味上與我國明清以來的孔廟確實有相當大的距離,與本省孔廟的繁瑣裝飾來比較,距離更遙遠了。
杏壇與大成殿的這個四合院是大正年間由日本的中國建築權威,伊東忠太教授所修復的。伊東博士在我國也很知名,也是我國古建築研究的開拓者之一。他修孔廟,據記載是依原樣修復的。但民國初年的修復觀念與今天大不相同,他修孔廟乃用鋼骨水泥取代木材,顯然只保存了當時的形貌。可見古建築的修復在觀念上見仁見智,有相當歧異。混凝土的柱梁上很久沒有塗油漆了,多處斑駁,不太順眼,我就與同行的日本友人談到這個問題。他們不能了解我的觀點,也看不出為甚麼木結構的古建築不能用耐久的混凝土修理。但他們笑著說,他們是外行,所以表示的是外行意見。
自杏壇前的廣場返身回顧,只感到下面一片綠色,靜寂之感與寺院相近。我不禁在想何以日本的孔廟會有如此大的差別。就以色彩來說,日本江戶時代的建築並不是崇尚黑色的。有名的觀光區日光地方的佛寺,其色彩之絢麗與裝飾的堆砌,即使是中東地區的宮殿也比不上。把孔廟改漆為黑色,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,有意要與一般寺廟所流行的紅色劃清界線。
推測起來,也許孔子的祭典在日本並不是國家正式祭典的一部分,孔廟又不是官學,所以孔廟的建築就沒有一定的限制。他們稱之為聖堂,就表示發自內心的尊崇,超過了制度與形式。他們使用的仰高、入德、杏壇等名稱,反映了知識分子的見解,與他們對孔廟建築的看法。或我國,由於孔子被追封為王位,連皇帝都要做形式上的祭拜,孔廟的制度相當官樣化,在主軸上使用櫺星門、戟門、大成門、大成殿、啟聖祠等名稱。櫺星門外尚有泮池。日本人沒有這樣的包袱,反而可以就他們自己內心的感受,及對儒學的體會,來解釋孔廟的建築。坦白的說,異邦人發自精神的表現,比起我們純形式的孔廟來,要動人得多了。
在仰高門與入德門之間,有一講堂,是純日式的建築,相當於明倫堂吧!在這裏有定期的中文或儒學課程。講堂旁邊,有一座高大的孔子立像,遠看去,覺得面貌與造形都很熟悉,原來是三年前臺北市贈送的,使我有點遇到故舊的感覺。該像坐落的背景很恰當,以綠色的枝葉為襯,是很受看重的。
松岡美術館的古陶瓷
東京的門牌系統,在臺灣的中國人是很熟悉的。那就是先有區,再有丁目,再有號碼。若干年前,我第一次到東京,住進旅館就拿出一份友人的地址,請櫃臺的服務人員告訴我怎麼可以聯絡。他們說除非有電話號碼,在東京找一個陌生的住址是很困難的。東京的門牌好像只有郵政局當地的郵務員熟悉。他建議我最快的聯絡辦法是打電報。這辦法果然有效,我的朋友當晚就接到電報,第二天就打電話到旅館來了。(當時我的朋友尚在念書,家裏並沒有電話。)
以後雖去東京多次,訪問參觀多半在事前安排好,或有朋友帶領,沒有遇到過找地址的問題。這次去東京,機票的安排困難,不得不多逗留一天,因此行程稍鬆散些。為充分利用機會,決定自行訪問幾處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民間文教機構,雅興有了,就不得不面對尋訪的問題了。
原來日本有些文教機構是私人設立的,規模不大,所典藏的圖書與文物卻很珍貴。研究中國文物的專家大概對他們都耳熟能詳,而一般的日本人知道的卻不多。在我們寄榻的旅館附近看到松岡美術館的一張廣告,正展出中國古陶瓷,覺得應該是很適合的去處。向日本朋友打聽,他們都率直的表示一無所知。看他們毫無興趣的神情,不打算再麻煩他們陪行了。試試自己在東京訪古的本事如何。
東京的門牌系統傳承中國古代坊里的觀念,是用行政區劃的名稱來做綱領,是面的系統,與後世用街巷的名稱做綱領之線系統大不相同。面系統只能告訴你約略的位置,很難按圖索驥,是很古雅,也相當落後的。我很佩服日本人保存傳統的精神,直到今天,大街竟都沒有起名字。
松岡美術館在一條大街上的高廈裏,離華航辦公室不遠,照說不難找。但是我們能夠順利找到,乃因向沿途的一家文物店打聽的結果。說來也是運氣,我們幾乎要轉向了,竟看到這家古董店。
松岡的中國古陶瓷收藏很了不起(圖4)。尤其最近幾年,投入了很多資金,大量收購高品質古文物。展出的量雖然不大,但品質非常好,堪稱世界第一流。不但大陸展出的僅具有考古價值的東西無法與它相比,即使歐美大博物館中的展品,恐怕也略遜一籌。我國的故宮博物院,元代以上的收藏很有限,像這樣高品質的唐、宋、元代作品,實在應該大量的編列預算去收購,尤其是最近若干年,由於中共的大量發掘,世人對中國陶瓷的興趣,早已自明清上推到漢唐。中國古文化的盛期展現的壯闊的創造力與灑脫的風韻,實在令人神往,比較起來,明清的官窯之纖細軟弱,實在不足以引為驕傲的。
松岡博物館在中國文物收藏上是比較新的機構。松岡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,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發了戰爭財,成功的企業家收藏美術品是世界的通例,松岡也不例外。年輕時喜歡現代繪畫,可惜其收藏在東京大地震時被焚。年事較長,才喜歡古代美術,對中國古陶瓷發生興趣還是最近的事了。至於他公開收藏品,設立博物館,也不過六、七年的歷史。
這使我想起即將關門的國泰美術館來了。
在歐美,私人開設的博物館很少。有錢人的收藏品早晚都捐到大規模的博物館去了。有些很有錢的人,甚至捐給博物館加蓋展示廳的費用,以展示自己的收藏。日本與我國的情形近似,有錢的企業家,購藏的美術品或古代文物,喜歡自己保存,因此每人都在想建造一座博物館。這樣做原也未可厚非。但是博物館是慈善性服務大眾的組織,雖收門票,卻是賠錢的。企業在賺大錢的時候,維持一座小博物館是輕而易舉的,一旦經濟情況發生變化,很可能面臨關門的命運。
這種博物館要保持永久,實在是很困難的。國泰美術館關門後,恐怕美術品都要出售還債了。這當然表示我們沒有法令的約束。日本人有博物館法,執行似乎也不太嚴格,但他們成立財團法人式組織,使博物館具有脫離企業的地位,使它不至於受到經濟情況變動的影響。即使如此,長久的投入人力物力,除非有相當穩固的基金,是很難辦得到的。這在我國,幾乎無此可能。大企業家都希望在回饋社會的事業上,能收能放,所以大多仍只能把這些事業抓在自己的手上。因此私人博物館到目前為止,談得多,做得少,即使未來大量的設立,恐怕都難免國泰美術館類似的命運。
大倉集古館的石刻
自松岡美術館出來,想順便到附近的大倉集古館看一下。大倉集古館是很有名的私人古文物收藏機構,很久就想去瞻仰一番而找不到機會,難得此行有點空閒,就不打算錯過了。
剛巧天公不作美,竟下起雨來了。我們趕緊搭上一輛計程車,請他帶路,一時忘記日本計程車的本領是有限的。這位司機先生不知大倉集古館在何處,但知道有一家大倉旅社,就向那個方向前進。由於語言不通,就把該館的地址拿給他看,上面寫著區、丁、目等,他老兄顯然茫然不知如何走法。甚至連大倉旅社的大門也找不到。轉了半天,依我推想他找不到的,就請他停車在一座教師會館之類的建築前面,冒雨進出詢問。警衛室的人員很客氣,但看了地址仍然無法指出方向。難得他熱心幫忙,打了電話給大倉集古館,又搬出那一帶的地圖,才弄清楚地點。我們按照地圖,找到自己的位置,發現計程車帶我們繞了一圈,距離並沒有縮短。索性買了把雨傘,踏著雨滴去尋雅了。
大倉集古館果然在大倉旅館的前面,是自一個小巷子進去。該旅館是很有名的,也算是車水馬龍,但很少幾個人注意到大門旁邊那座小博物館的。這也難怪,集古館的圍牆上寫了斗大的英文字,是大倉旅館,甚麼人會去注意小牌子上的字呢!
創館的大倉先生是明治時代的人物,為當時的大企業家,也是受封的貴族,對明治維新似乎有相當的貢獻。生前收集了不少的文物,去世後,由其第二代設館公諸於世,為日本第一座私人博物館。館的四周為院落所圍繞,陳列著來自中國與泰國的石刻,相當可觀。其中也有大倉先生的雕像(坐著讀書的銅像),及紀念其豐功偉業的碑文。依大倉當年的氣魄,局面顯得侷促些。恐怕因為後代有經濟的問題,不得不以大部分的土地建造旅館之故吧!但卻不免使我感到,即使在如此尊重文化資產的日本,在現實的壓力下,文化的設施也是很寂寞的!
該館是二層樓的建築,也是在大地震之後,由伊東忠太博士所設計的中國式的建築。屋頂是廡殿式,瓦為銅綠色,脊上的吻飾很簡單。伊東對中國建築非常熟稔,如果有些不合規矩之處,也是他有意修改的。地面層為石砌面,並有拱圈,是所謂東西合璧的作品。大倉把集古館蓋成中國的式樣,可知對中國文化的尊崇。我注意到入口處的匾額是民初中國的政要徐世昌寫的。
與外觀比起來,內部的陳列品多少有點使我失望。既然館的式樣是中國的,裏面應該陳列著中國文物吧!事實不然,中國古物只有少數幾樣而已。記得在過去讀過的介紹文字中,敘述大倉集古館曾受東京大地震的災害,損失了不少寶貴的古物。中國古物的收藏是否因此而遭到破壞呢!
所幸我最關心的一件石刻仍然陳列在那裏。我知道大倉集古館的名稱,乃因伊東忠太所著的中國建築史上首次提到這座佛像。這座像特別之處,在於其背後刻著甚多建築物之形象,簷角起翹誇張,如同牛角一樣。據伊東當時的推斷,認係東晉之物。由於該像來自河北涿縣永樂村東禪寺,應該是前燕所轄之地,時當紀元四世紀。由於建築史家一直認定中國建築的飛簷開始於南北朝末或唐初,這塊牛角形出簷的石碑,就使他們大傷腦筋。伊東認為誇張的簷角只表示簷端之彎曲裝飾物,相當於鴟尾,並不能推翻南北朝末期產生飛簷的學說。
後來我在伊東另外一篇文章中,看到對此碑年代的推斷,向後延伸了兩個世紀,認係六世紀時北齊之造物,有多種遺物顯示中國建築已有翼角起翹之現象,這樣歸類,當然可以便利於支持已有的界說。我曾在拙著《斗栱的起源與發展》一書中,根據此碑上屋頂的造形,討論其宗教意義的可能性。
這次親眼看到這座雕像,以重要文化財的資格被維護著,心中充滿了不虛此行之感。但是看說明簽上指示的時代則改為五世紀的北魏,必然是有根據的。最近幾十年來,由於遺物發掘的數量很大,南北朝時代的文物斷代多了不少證據。這座石碑刻有大量的圖案與人物,推斷正確的時代應該是不成問題的。然而這可以說明對古代人物的研究是很困難的。
我在雕像的前前後後走了幾遍,覺得應該攝影以供參考;而大倉集古館是禁止攝影的。與守衛人員商量,他們要我與管理員商洽。幸虧遇到一位物理學教授也在參觀,他能說英語,可以經他的翻譯說明來意。管理員表示同意後,我使用了最後兩張底片,留下了值得寶貴的紀錄。
(圖片:大倉集古館的北魏石碑)
靜嘉堂的木刻版書
這次去靜嘉堂文庫則是很偶然的。知道它的存在乃因翻閱讀書目錄時,發現它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古版書。我並不是讀古書的人,但近年對古典風水有興趣,不時注意這方面的古書,曾在它的目錄中發現有兩部明代中葉前的木刻版風水書,因此靜嘉堂這個名字就一直記在我的腦子裏,後來在翻閱中國古代美術的著作時,有兩個精美的唐三彩器,下面註明屬於靜嘉堂文庫。這當然加深了我的印象。
前些時候我曾打聽取得那兩本古風水書複印本的可能性。由於與日本的學術界毫無淵源,隨便打聽一下,並沒有甚麼結果。因此使我感嘆做點研究是很困難的。這次去日本另有公務,雖然抱著渺茫的一點希望,並沒有訪問靜嘉堂的計畫。只是在聊天時,一位日本朋友問我公餘有無其他的打算,我不經意的說,如果可能,很想去靜嘉堂找兩本書,他大為驚訝,我為甚麼知道這樣一個偏僻的所在?
實在巧合,他的家就在靜嘉堂文庫附近。大部分的東京市民都不曾聽說過這個名字。因為這個機構坐落在住宅區中的一個公園裏,只有住在當地的人偶爾去散散步,才會注意的。當然,我的朋友大概不知道這文庫有厚厚的一本中國古書目錄,在漢學界可能是世界聞名的。他聽了我的解釋之後,表示可以利用午飯前後的時間,順便訪問一下。他認為我的訪問路線相當配合。
靜嘉堂坐落的住宅區,道路狹窄曲折,七彎八轉,才到達那座近似原始林一樣的公園。如果不是朋友帶路,無論如何是找不到的。走上濃蔭夾道的一條小路,再轉一個彎,才看到兩座飽經歲月的老房子。車子就在砂子鋪地的停車坪上停下來,使我感到繁華的、處處標榜二十一世紀的東京市,忽然在眼前消失了。
其實這文庫的房子並不真老,看樣子也不過二次大戰前的建築,只是在叢林之中的極靜,予人以時代的錯亂感而已。靜嘉堂與大倉集古館相似,都是日本現代化初期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積藏,後經公開者,所以建築環境都代表當時的趣味。
靜嘉堂分兩部,一座日西合璧住宅形式的建築,規模較小,是中國陶瓷的陳列室。此非我此行的目的,但既來了,就順便看一下。當時正展覽唐三彩。數量不多,但品質甚高(圖5)。靜嘉堂展出的三彩馬、駱駝、神將與鎮墓獸等,原是相當常見的器物,但其尺寸特大,雕塑精美,為國內所無。故宮博物院並無唐三彩藏品(有三、二件贈品),歷史博物院所藏品質中等,如馬,不過一尺左右的高度,靜嘉堂所藏屬於二尺半以上的大件,實在驚人。這裏的一件不太起眼的白底貼花滴藍彩罐子,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。又有一只真物大小的三彩鴛鴦,一對守護獅子,被指定為重要美術品,都精美異常,令人感動。看了這樣水準的東西,不免覺得當年我們自己不懂文物的可貴,為外人廉價取得,實在是很丟臉的事。政府應該編夠預算,設法搜購國外民間的重要文物才好,不可再任其流入外國的博物館裏了。
靜嘉堂的文庫是一座外觀平實的三、四層建築,大約是書庫的面貌吧!進口處亦很不顯眼,門是緊閉著的。按門鈴數次,才有一位女士出來詢問來由。我遞上名片,由同行的日本朋友解釋,終於得到管理人員的許可,容我們入內。
室內陰暗,是深色木板鑲裝的西式建築,一邊有壁爐,上懸創辦人的畫像。面積不大,應是明治時代的遺物。因係西式地板,我們要脫了鞋才能進去,靜嘉堂文庫為重要文化財,室內不准抽煙。我搞不懂是指這座房子為文化財,還是指庫內的藏書?請教那位朋友,他搖頭笑笑,根本不知道文化財為何物。
我們被引進一間明亮的大房間,有兩個大窗戶面對院落,很像當年的書房。裏面有二、三人踞案研讀。我們進門後,先要登記,然後填寫單子,要求取書查閱。這個手續似乎與中央圖書館的珍本書取閱方式相類,只是日本人在形式上顯得更加謹慎小心而已。
因為時間匆忙,我就不客氣的說明來意,自目錄中查出那兩本風水古版書號碼,請她拿出來看看。我以為她會像中央圖書館一樣,讓我看微粒影捲,那知過了一會,她把原書捧出來了。並告訴我說,其中的一本是很珍貴的。
她指的那一本是很普通的《葬書集註》。在目錄上寫著明新刊本。我想看這一本書,乃因《葬書》流傳甚廣,各版本均來自明末,也有文字的不同。同時我很懷疑這本書的來源,一直想知道是否明新人所杜撰的。明新刊本應該可以解答我部分的問題。經看到原本,發現這書不是明新刊本,恐怕至少屬於元代的遺物了,因為明新儒者宋濂先生在書前有夾頁的批文。照常理推斷,他在書前寫批,在當時應該已是古書,所以靜嘉堂把它歸在宋版書一類裏。這樣說來,南宋已經有《葬書》是可以肯定的了。
她同意我可以申請影本,但因他們沒有影捲,沒有現成的複印本服務,影本的製作非常昂貴。尤其是宋版書,每複印一本再加約臺幣一千之費用。折算起來,印一本沒有多少頁的書,竟要數千元新臺幣了。考慮了一會,覺得也沒有選擇,只有拜託她代印了。我們辦了手續,辭謝出來,她把我們送到門口,行禮如儀的,才告別而去。我感到了卻一樁心事的愉快,公園裏的鳥聲居然也很入耳了。
(後記)本文發表後,承中央圖書館蘇積先生指正,靜嘉堂文庫之《葬書》仍應為明新版,後再向該堂查詢,同意不照宋版書收費,蘇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