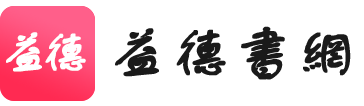報應,這個詞彙容或起於佛教東傳;但善有善報,惡有惡報的思想,卻應是發端於渾沌初開的原始先民時代。我國典籍最早的記錄則見於《易.文言》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;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
但現實生活往往不能盡如人意,甚至常讓人發出好人不長命的慨嘆。然而,難道就因現實的不如意,使我們放棄為善去惡的信念嗎?當然不能。哲學家們、文人墨客各從不同的角度強調善仍是人生至上的皈依。哲學距離我們平凡大眾太遙遠;小說家言、稗官野史才貼近我們的生活。文學家們便藉一枝彩筆,為我們確定善惡因果的必然性,提挈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心,不致淪落到罪惡的深淵。
因果論在哲學理論中原有各種複雜的說法。但報應觀念將因果論化約為簡單的有某種行為為因,必然相應的產生某種結果。而且在報應小說裡通常是由果推因,人們總是在看到結果出現,才儼然以預言家的姿態告訴眾人:瞧,這就是因果報應啊!
六朝志怪開始,中國古典小說中因果報應的題材便已屢見不鮮。最初,如顏之推《冤魂志》、劉義慶《宣驗記》等書書旨明確,乃為宣說佛教教義而作。故事內容多為經像顯應,或借鬼魂以明報應之必然。隨著小說的發展,內容與形式都愈加繽紛繁複,報應之說已不再是佛教的專利;報應的方式則大概歧分為天命、神鬼、三世輪迴三類。這是原始宗教及儒、道、佛三教雜糅的結果。
天命在雜亂的自然神信仰時期是指天的意志,天具有人格神的意味。人格天的觀念是人類原始社會的普遍現象,中國則在殷周之間多神的原始宗教時代,對於天帝賞善罰惡的信仰即已植根於人們心靈深處。天以祂神的地位,無上的權威,主宰著芸芸眾生的禍福。人們則由於對天災人禍的恐懼情緒,而絕對地皈依天的支配。周初人文精神逐漸覺醒,試圖扭轉人們對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恐慌。在宗教性的天人關係中注入人文理念,賦予道德的意義。天的意志雖然仍具有權威,但扣緊了人事的善惡。所以祂不再是不可捉摸,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來把握天命神意的降臨。天與人成為平等的存在。但是,為善天報之以福,為惡天報之以禍畢竟只是人文化的理想,情感上的希冀。天的意志有時是不合乎理性的。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殘民者昌,佑民者殃。
儒家思想的出現,使天命更不僅具有道德的意義,而是它本身即為道德的根源。順著這條思考路向,儒家解決現實上福報不一的方法是將問題劃分為二:一是將它歸於不可知的被決定的命運之命,而說死生有命,富貴在天;二是出於自由意志,承擔無所逃於天地的道德實踐責任之天命。然而這終究是屬於哲人的思考;對平凡的大眾而言,哲學的解釋並不能消解他們心中的不平。原始宗教的信仰受了人文精神的激盪而轉化,但宗教不能被取消,實際人生中的困阨仍待宗教來解決。
道教思想來源複雜。主體有二:一是依託老子為始祖,將老子的自然曲轉為虛無。二是秦、漢方士的神仙和陰陽五行之說;又摻入自然崇拜、符命星相等。經典則抄襲儒佛。所以它本身即是三教合流的產物。但原始宗教之信仰鬼神,起於對茫昧不可知的自然物的恐懼崇拜;道教則一方面認為鬼神有禳災解禍的能力,而以祈禱的儀式與鬼神交通。鬼神介於天人之間,代天降災降福於人,也代人向天祈求免除災難。另一方面,道教一個基本教義就是追求不死的境界,認為人可經由自我修煉保存形體變化為神仙,而行服食導引之術。受道教思想影響表現在小說中的善惡報應觀,即因這兩方面又歧分為鬼魂報應及升仙。
鬼神並非道教獨有的觀念,但是集先民以來山川萬物諸神鬼之大成的,卻是道教。並建立了一套階級森嚴的神仙譜系。儒家雖說敬鬼神而遠之、不語怪力亂神。但儒家思想從先秦以迄宋、明,自有一套特殊的鬼神觀。約略言之,鬼神並非人死後另有一個形體或精神存留;而是生者對死者的思念存想。儒家特重祭祀之禮,也就是因生者的思念存想,來感受死者彷彿精神復活。所以儒家之談鬼神,實際上也可以說是無鬼論、無神論(相對於有形體存在的鬼神論)。佛教講六道輪迴,其中有地獄道、餓鬼道。初傳入中國時,為了宣教,造作了許多地獄、鬼魂的故事。也有畫家施諸丹青(如吳道子有名的《地獄變相圖》),描寫繪畫出恐怖的地獄形象。
在小說裡,鬼魂報應通常表現惡報。被害者成為鬼,這鬼受上帝(在道教的神仙譜系裡稱為天尊)的管轄,卻可以脫離人間法律的束縛。它們或奉上帝的旨意到人間敦促執法者行公理;或乾脆直接對惡人施懲罰。
升仙則通常表現善報。人們對死亡懷著恐懼,從原始先民即希冀著肉體的長生不死。於是建構了一座神仙不死的樂園世界。經過漫長而複雜的過程,發展為道教的宗教化體系。道教的信仰者對神仙樂園懷有堅定的信念,絕對相信它真實的存在。除了建立龐大的神仙譜系;並極力塑造描繪神仙所居的樂園;更進而形成一套凡人修煉成仙的方法,即所謂外丹、內丹。簡單的說,外丹是靠外在的物質煉養身體,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煉丹服食。內丹則是以靜坐或各種動作修煉人體內的氣。
這一套神仙理論和社會通俗倫理道德結合,以行善↓成仙的簡約的因果關係,形成了道德上的禁制要求。小說描寫成仙故事,意義即在於此。
因果與輪迴在佛教義理中,原是分別解釋大千世界生命現象的條件關係,及生命活動流轉的歷程。理論根據則是靈魂不滅。做為一種思想,它成為知識份子研究的對象;但做為一種宗教信仰,抽象的義理無法深入民間。因此佛教在傳入中國之初,即以三世因果及六道輪迴的悚動道理,附於黃老神仙之術,以達到傳教的目的。而這些粗淺零星的道理,恰能接合民間原始宗教信仰天命意志主宰人間善惡報應的觀念;也為現實人生福報不一致的不公現象,提供了解釋的依據。
所謂三世因果,是說人在現世的一切遭遇,都是前生行為的因所得的果;而現世的一切行為則為來生一切的因。現世若未得到合理的回報,則來生或二生、三生乃至百生必然有所結果。所謂六道輪迴(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道、畜生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),則是借天堂地獄的對比,警惕世人生時的作業(活動的結果)與死後的歸向有關。
在哲理的立場,因果與輪迴是要破除人間的無明執著,則能解脫輪迴而入涅槃之境。當與民間通俗文化結合,則是以神道設教,借此鼓勵人行善去惡,求得福報,避免惡報。
報應觀念便在原始宗教賞善罰惡的天命意志基礎下,融入儒家的人文思想及道、佛的通俗教義,而形成更完備的解釋系統。在一般群眾的生活中,實踐道德的力量不是來自自覺的反省,而是因有鬼神在天的權威下監督人間的善惡。人們畏懼天的懲罰及為了向天取得報酬而遵守道德規範。當現實並不如預期的福善禍惡時,則採取安命的態度。但這種態度仍然不是出於自由意志,而是藉三世輪迴來拉長報應的時間,以平服心中的遺憾。
小說文學在實際人生之外別造一個奇詭的舞臺。它所展示的人們的情感世界,有時卻又比真實人生更真實。尤其是中國古典小說,舉凡俠義公案、神魔鬼怪、愛情世態等,無不在作者筆下幻化出一片絢麗的天地。報應小說之為中國小說中的一類,雖然從六朝志怪即已見其迹;但一方面小說這種文學形式初萌芽,我們雖稱之為志怪小說,其實多是篇幅短小的傳聞異錄。結構簡略,事件單一。另一方面則如前所言以宣說佛教為主,所謂神道設教的意味濃厚。
到了唐朝,儒、佛、道均已各自建立體系,在思想界中遂互有衝突、反省、批判。由此延續而產生對宇宙人生重新認識的一場哲學突破。這場突破主要的成就是體認到天命的超越性而敬畏之,並因此確信天命宿定。小說作者在這種哲學思考轉變的環境中,也於傳奇作品展現一共同的主題對天命的覺知與肯認。他們所覺知的天命沒有人格神式的主宰意義;但因它是超越的、根源的,所以小說中即使言成仙成佛、鬼神靈驗或三世輪迴,最後也是歸結於天命。因此因果報應在唐傳奇中,只能說是天命觀的附屬系統,而不是獨立地、對人事興動的解釋。(註:唐朝哲學的突破及其與小說的關係,參見龔鵬程《中國小說史論叢》<唐傳奇的性情與結構>。台北,學生書局。)
宋明話本以市井文學的姿態出現。如果我們說唐傳奇代表了中國的雅文化;那麼話本就代表了中國的俗文化。傳奇人物,男子或如虬髯客的恢宏豪放;或如崑崙奴的行俠仗義。女子或如霍小玉、崔鶯鶯的執著愛情;或如謝小娥、紅線女的堅忍貞潔、正氣凜然。話本人物則多卑微瑣碎,汲汲營營於自身的衣食起居。他們相信冥冥中鬼神監督著人間的道德倫理與善惡行為。因此道德意識對他們而言,不是君子的自我要求;而是日常行為中去禍求福的一種約束力量。故話本人物兢兢業業謹守著通俗倫理,但求平安過一生。假如世事竟爾波折起伏,也只有流淚痛哭,自悲自憐一番。然後不是認命的相信那是天意安排;便是將它歸於前世的因果;或很鴕鳥的寄託於來世。
三教思想合流在話本中一覽無遺。
這裡所選十篇,依時代言,<苦兒徐鐵臼>、<鵲奔亭>、<兄弟與長工>屬六朝;<三世精魂>、<血跡衫子>是唐代的作品;<巧禍>、<團圓>是宋代話本;<六月飛雪>原是元代的雜劇;<太行山少年>、<灌園叟升仙>則是明代的擬話本。報應觀念在這十篇中表現的方式,有人格神式的天命意志;有冥數前定,定命式的天命;有鬼神現身;有三世因果輪迴。四者或單獨架構整個故事;或交互運用以成篇。
對人格神的信仰,在小說中已非原始宗教的形態;而是在經過人文的洗禮後,沉入人們潛意識的一種表現。不需經由什麼特殊的溝通儀式,而直認宇宙仍有一主宰在傾聽祂的子民的陳訴。例如<六月飛雪>一篇,竇娥在臨刑前向天發出凄厲的誓願,就是將在現實人間所受的冤屈,投訴於至高無上的天,而天也恰如其願的有了回應。那並不是一段荒謬無稽的神話,它表現的是人們尋求公理的強烈意識。公理迷失於人間,但超乎現實世界之上還有個權威在朗照天地,昭示著人們;真理還須由天來裁決。
至於定命式的天命,更顯人文的意義。在經過對天人關係的沉潛思考後,所謂報應,是命運前定;是對天理的認同。如<血跡衫子>中的郭氏將血跡衫子出現而夫仇得報,歸之於天意;<巧禍>和<團圓>中一連串的巧合,都是天理,更無須藉神話情節阻絕人們的理解而產生荒謬感。因為偶然與巧合都是人生中經常可見的,卻又不是人類的理性所能解釋。唯有高居於上觀照現實世界芸芸眾生的天,有能力操縱這一切。
但這種命運前定,又不能視之為宿命。因為在以巧合為主要結構的小說中,天有如一隻陳藏著的手,操縱著故事中各角色的命運,完成報應的結局。但若作者無意借巧合來架構成篇,則混雜了原始宗教對自然物的崇拜、佛教的靈魂不滅、道教的諸神譜系等思想的鬼神觀念,便適時取代了那隻隱藏的手,現身來執行天意。在這類小說中,彷彿宇宙被三分天下天、鬼神、人。鬼神與人的關係更為密切。如<鵲奔亭>、<兄弟與長工>以鬼魂自訴的方式達成對惡行的懲罰,只表現了鬼和人的關係。在<苦兒徐鐵臼>和<灌園叟升仙>中,則天與神鬼及人脣齒相依甚為明顯。徐鐵臼的母親向天訴怨,得了天庭的符旨而來報仇;灌園叟則是由奉了天帝旨意的司花女神來度脫。這個天,儼然是掌管人間善惡,維持宇宙秩序的公平裁判者;鬼神則是天與人的中介,代天監督人間的善惡,並奉天意來執行賞罰。
當天命與鬼神都不足以解決人間的困惑,因果輪迴遂成為另一塊解釋生命現象的根據地。如<三世精魂>一世被害;二世索債;三世討命。<太行山少年>則在二世便已了結前生的冤業。
翻翻《太平廣記》報應類所敘的故事,報應結果大抵不出生命、健康、財富、地位。這些在現實中都是人們最希望得到;最畏懼失去的。善報便是讓行善者或長壽、或惡疾不藥而癒、得一筆橫財、官運亨通。惡報則是奪其壽數、患病痛苦、窮困潦倒等。
十篇中,<灌園叟升仙>和<團圓>是善報。前者表現道教思想的修煉成仙;後者以夫妻團聚作終。其餘八篇都是惡報,且都是以生命償報他們造的惡,所以往往鮮血淋漓。作者當然不是以血腥的刀光劍影來譁眾取寵,而是他們相信:愈悚動驚人,愈能激起人們對善惡報應的信仰。
報應觀念從我們的遠祖時代發芽生根,逐漸茁壯。到現在,報應一詞仍不時在人們口中流動著。
積善之家必有餘慶;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原是中國古代宗教精神人文化的一個明證。它說明了人不需向飄渺的上帝或神祈求眷顧,自身德行的善與不善便可決定吉凶成敗。但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自有雅、俗之別。當雅文化由所謂士人擔任傳播者,步步下降到民間社會時,它的理想性便會因與現實人生衝突而淡化。儒家道德的理想性是建立在良知的基礎上,它是義所當為,原沒有功利可言。但當儒家思想主導著中國人的生活時,民間也同時吸收了佛教初期粗淺的道理,和雜糅的道教的觀念。道德便逐漸與功利結合。人們行善,不因善是人間至理,人類高貴的本性;而是希冀得到某種酬報。去惡,也不因惡是人性的沉淪;而是恐懼遭受某種災禍。
報應觀雖是三教合流的民俗思想,毀損了儒家原有的活潑精神。但在這科學文明主導一切的時代,融合了天命宿定、鬼神現身及三世因果的報應觀,指出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軌範。這仍是值得慶幸的。